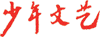|
|
黑星
作者:舟 卉
陶璐是东明中学初三(2)的学生。她坐第一排靠窗的位子。陈文峰是她的同班同学,坐教室后面靠近扫帚畚箕的位子。他初二那年才转学到陶璐的班上。
一条很直的对角线。陶璐回头望不见陈文峰的脸。隔着那么远,谁也没有想到陶璐会和陈文峰好上。
陶璐是个很漂亮的女孩,有一双挺大的双眼皮眼睛,睫毛老长,翘翘的像蝴蝶栖落时的翅膀。她沉默孤僻,不大爱说话,成绩也不好。上课时候无精打采,下课了也蔫蔫的。王可清老在背后抱怨:“和她同桌,真是受罪!简直要闷死了!”
“不会吧,没那么夸张吧?”
“怎么不会!你看她那双眼睛,死气沉沉的。有一回我午睡醒来,她直直地盯着我,眼睛里黑咕隆咚没一点光泽。我心里惊了一下,你知道我当时想到什么?”
“想到什么?”
“坟墓。她那排睫毛就是坟墓上的两把蒿草,什么时候仔细看看她的眼睛,你肯定会说像。”
“别那么损吧,你知道她心情不好,她爸妈去年离婚了。”沈燕忍不住插进来。
“离婚了又怎样?沈琼父母不也离婚了,张岩岩她不也是单亲家庭……”
“嘘———”王可清看见陶璐走进教室来,连忙把食指放到唇上,示意沈燕别再说下去。
陶璐总是一个人上学,走路时头低着,从来不和同学一块儿走。中饭在学校食堂吃,买好菜坐在角落里一个人拨着。原先她也有几个好朋友,可现在一个都不剩了。她们说她很怪,跟大伙儿不一样,连沈燕也很少再和她说话。她很少参加集体活动,遇着运动会或文艺演出不是推说肚子疼就是说嗓子哑了。可谁都知道,她小学时曾是校体训队的种子选手、校大队的文艺委员,得过区歌咏比赛一等奖。
班主任杨月华对陶璐的变化颇为诧异,初一时找她谈过话。陶璐什么也没说,只用冷漠的眼光盯着老师,直直的。班主任后来也放弃了。成绩差的学生本来就不怎么受器重,陶璐的沉默更让许多老师对她忽略了。开家长会时,陶璐的父母从来不到。第一次杨月华还问过陶璐。陶璐满脸漠然,只说她也不知道。后来杨月华通过别的学生才知道那阵子陶璐的父母正闹离婚。
初一下半学期,法院调解无效,陶璐的父母终于离了。她判给了母亲。父亲陶泽海把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留给母女俩,自己带着那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去了另一个城市。
陶璐的记忆里,小学五年级起家里便开始发生变化,以前只是隔三差五吵一次,后来几乎是天天吵。母亲脾气躁,常常吵着吵着就把饭桌掀掉了。父亲打母亲耳刮子,母亲像疯女人一样扑过去又抓又咬。陶璐起初只会捧着饭碗躲在墙边哇哇哭,不知所措,又怕又慌流过很多泪。有一次,一只镂花的玻璃杯飞过来,正好砸在她脑门上。玻璃杯碎了,她额头砸了个坑,血汩汩地冒出来。从此,她额上留了一块灰褐色的疤痕。杯子是父亲扔的,因为歉疚后来一段日子他天天很早回家,陪着陶璐哄她开心。可等陶璐伤好了,他又逐渐不再过问女儿的一日三餐,甚至连她的生日都忘了。平静了几天的家,重新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。
这次父亲提出要离婚,态度决绝。离婚大战拖了三年,其间不是摔盆砸碗就是无休无止的冷战。陶璐慢慢习惯了,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。每回母亲音量一提高露出了点火药味,她就逃进自己的房间,“砰”地踢上门,捂住耳朵钻到被子底下,把枕头也压上。或者,拿了钥匙,干脆就到街上去游荡。等家里的两个人吵累了、没声响了,再小心翼翼扭转锁孔,鬼影似的溜进房间。
父母不和以来,陶璐没再带同学到家里玩过,也矢口不提到父母。每当同学们说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如何如何时,她只是默默地避开,从不加入那个话圈子。
离婚前母亲时常躲在家里以泪洗面,她是受害者,陶璐觉得她可怜。但离婚后仿佛变了一个人,再也没见她流过泪。“没有你陶泽海,别以为我会过不好!除了你姓陶的,我就不信天底下没男人了!”父亲早不在了,母亲翻箱倒柜从抽屉底里挖出原来的照片,一边撕,一边咬着牙根骂。
很快,母亲有了新的男友。陶璐见过那男的,竟比母亲小十岁。陶璐不知道母亲是报复心作祟,还是真的爱那个陶璐只能喊成大哥哥的男人,反正,她只觉得恶心。母亲第一次把那男的带进家时,陶璐当着他们的面狠狠掼了一只杯子。
“哐当!”明晃晃的碎玻璃四处迸溅。一颗碎屑飞到母亲脚背上,割破了丝袜,有血渗出来。陶璐狠狠刮了母亲一眼,又狠狠白了那男的一眼,一声不响走进房里去。“砰!”死命把门给踢上。
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,陶璐每次上学放学总觉得背后有许多双眼睛睃着。离家越近她就越害怕,只要见到弄堂口有两个女人在碰着头说话,她就心里发毛,立马想到她们也许是在说母亲和她。有一回是她亲耳听见的,居委会的柳妈和小卖部的老板娘钱婶在嘀咕。
“你说陶泽海的女人咋变得那么快?离婚还不到两个月,就往家里领男人了,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呢。”
“以前老骂丈夫有外遇,暗底下的事谁说得清。”
“她这回做事真的忒任性!小璐也那么大了。她也不避嫌,说不定人家小伙子看上的不是老的那个……”
两个女人聚在水龙头底下洗菜,蹲在地上,屁股向外撅着,笑声一浪一浪。陶璐从她们背后走过,那些话一句不漏地传到耳朵里,像针在扎,一种脚底板被戳穿了的感觉。她觉得虚脱,差点瘫在地上。她咬咬牙,抬起脚,鼓足力气向自家那幢楼跑去。撞上门又闩了保险,她靠在门背后喘气,一动也不动,脸煞白煞白,然后,便团缩在地上流泪。那咸涩的液体渗入嘴角,直发苦。
她很少再跟母亲说话。感冒发烧了也不说,自己胡乱地吃药。那个夏天她来了例假,血流个不止,肚子钻心地痛。那一刻她异常恐惧,希望母亲能回家帮她一把,她想再这样下去她会死的。但母亲连着三天没回家。陶璐把自己锁在房里,牙齿狠命咬着床单,把床单的一角都咬烂了。后来她痛厥过去,终于绝望了,心里想:“流吧,流吧,死个痛快!”她觉得自己差点被邪笑诡谲的死神牵了手去。
生活不是灰色的,而是黑色的。她讨厌自己的家,讨厌周围一切的人,甚至常常对活着也充满了厌倦。她小小的脑子里想过死,那是一个可怕的念头,但又是那样充满诱惑。
如果那年陈文峰不出现,她想她也许真的早死了。
初二下半学期刚开学,陈文峰转学到了班上。杨老师让他上台做自我介绍。他紧张得要命,脸憋得通红,说话也结巴了。台下一阵哄堂大笑。陶璐躲在窗下远远地望着他,没笑,忽然觉得他也可怜。陈文峰个子很高,干瘦干瘦的,发育阶段的豆芽菜型。有点土气,他自己也说了,刚从乡中学转来,在农村长大的,头一次到城里。
陈文峰插到班上后,很少说话,很怕羞的样子。头一阵新鲜过去了,班上的男生已不再爱跟他玩。第一次数学月底考,陈文峰不及格。全班就两人挂红灯,另一个是陶璐。
陶璐习惯了,无所谓。她照例很迟回家。教室里只剩她和陈文峰两个。陶璐理书包时听到“呜呜”的哭声,很轻的极力压着。她以为是窗子外面传来的,回头才发现陈文峰趴在桌上,头埋得很深,一颤一颤。她很惊讶。她第一次看见男生也会哭,而且哭得那样的伤心。不知为什么她心里一阵酸,很同情。虽然两人以前没说过话,陶璐还是朝他走过去了。
她伸出手去拍他的肩膀,只轻轻拍了两下,仿佛他是易碎的瓷片,用力了会碰破。
“陈文峰,你怎么了?怎么还不回家?”
陈文峰不理她,依然趴在桌上哭。陶璐又问他,他还是没反应。
陶璐心里急了,乱了,像有一千只一万只蚂蚁在啃在爬。她突然大叫了一声:“陈文峰,你到底怎么了?别哭了!你再哭,我也想哭了!”
声明:本文由著作权人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。
网友评论
相关链接
-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2005-04-11 10:39
- 不测是人生的一个险滩 2005-04-08 10:24
- 醒悟总是来得太晚 2005-04-07 10:07
- 和爸爸之间永远溃烂着的伤 2005-04-06 10:12
- 我们无法设防滑坡 2005-04-05 10:33